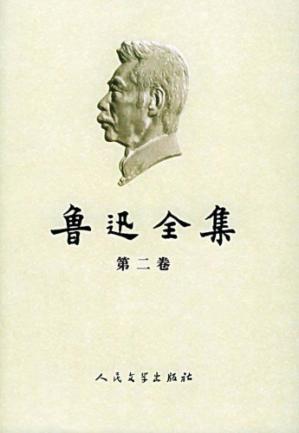电子书下载地址
鲁迅全集(第02卷: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鲁迅) .pdf
内容简介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在1922年~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这八篇小说分别是:《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外加一篇《序言》。此书主要以神话为题材,多数是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其中,《补天》写于1922年冬天,原题《不周山》,收录于《呐喊》初版,后改名《补天》并抽出;《奔月》、《铸剑》写于1926年和1927年,《铸剑》在《莽原》上发表时题名《眉间尺》;《补天》、《理水》、《非攻》、《采薇》、《起死》写于1934至1935年。
作者简介
鲁迅在1922年~1935年间,跨越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严肃,到油滑,到生死。
读书笔记
冀翼,80后写作者,思考者,公众号:妄想症患者病历本。欢迎订阅。
鲁迅《铸剑》内含的生命哲学
新时期以来,《铸剑》作为鲁迅的一篇重要作品,长久被评论界所忽视,只有残雪、莫言这样的文学创造者才对它产生了一定的偏爱,并且写过一些感性重于理性的分析文章。也许这恰恰证明,只有具备艺术精神的艺术家,才能对鲁迅最深层次的生命产生共鸣。
《铸剑》是否是鲁迅最深层次生命的展现呢?我门可以通过感悟,以及对文本细节与鲁迅的生命轨迹进行分析比较,来得出结论。
鲁迅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词汇,就是出走,他不只一次在各种文章里提到出走,例如《娜拉走后怎样》、《过客》等等,可以说,走、出走,是鲁迅思考的一个着重点。出走是鲁迅生命经历的一个焦点词汇。鲁迅“走异地,逃异路”去求学,为的是改变自己,改变社会。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这路应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是“封建制度的逆子贰臣”、“叛将”,证明他是从封建文化里“走”出来的“新”人。“铸剑”正象征着这样一个挣扎思考与锤炼的过程。
让我们来看一下,小说中的出走是怎样与鲁迅生命中的出走相结合的。
眉间尺出走去报仇时的年龄是十六岁,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但他醒着。他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而鲁迅自己于1898年4月底离家,5月7日到南京,入了江南水师学堂。算起来,正是十六、七岁的样子。
鲁迅在《呐喊 自序》中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而他当时写的一则戛剑生杂记中说:“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这“柔肠欲断”、“涕不可仰”的神态,真与眉间尺“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的形象相类。是一样地“不冷不热”的性情。
这次出走(现实中和文本里),都暗示了铸剑的开始。是觉醒的第一步,是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鲁迅人生中影响同样大的另一次出走,便是那次兄弟失和。这次失和而出走,在小说里的体现,便是那位黑衣人——宴之敖。
许广平的《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说:“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这次出走真正震撼了鲁迅的灵魂,表面上是与周作人的生活冲突,其实暗含着两种生命形态的不可调和,也廓清了鲁迅对于自己需要摒弃的部分之认识。兄弟俩从此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次出走,使鲁迅确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宴之敖作为眉间尺的成熟版,就是暗示了不同时期的作者自己。
两次对鲁迅的人生意义影响重大的出走,都反映在了小说中,可不可以说,鲁迅是把《铸剑》写作了自己的心灵成长文本?精神成长文本?我认为,通过分析《铸剑》,就可以基本厘清鲁迅的生命哲学。并且通过这样的分析,来承接鲁迅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科举案发,从此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而后,鲁迅就被寄养在大舅父怡堂处,据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说:“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这一年鲁迅12岁。
随后,鲁迅的父亲病倒,庸医胡乱而荒唐的用药,使父亲病死。其间,鲁迅每日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体验了耻辱与绝望。这一切,都使鲁迅绝望于中医而选择西医,对日后的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在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和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中说:“《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①
但是我认为,在人生的认知层面,鲁迅学医,以及之后的弃医从文,都是他要做事情、改变事情的表现。是他对“现实性”、“功利性”的重视与体现。鲁迅早期曾用笔名“迅行”,便是取快速行动的意思。这“行”便有“现实性”的意义。早年的经历,又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反对旧势力、旧礼教的叛将。一切加之其身的屈辱,都在努力寻求一个“现实性”的出口。于是,他终于寻得了——复仇。
复仇精神作为鲁迅的一种人生观,渐渐地演变成一种复仇哲学。因为鲁迅看到,只有将复仇精神提升到哲学(生命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地做到坚定的复仇,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些什么。而到最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其哲学与生命的高度融汇,而使得手段与目的相混杂。(此处容后文详谈)
二
鲁迅为了做事情,改变事情,追求现实性的改变,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复仇的坚定性、彻底性。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坚定与彻底。小说中,鲁迅通过眉间尺与老鼠的对峙,以及由[1]此产生的复杂情感来进行揭示,这种多余的自然情感是复仇坚定性与彻底性的首要绊脚石。
小说一开始,出现了两个角色:眉间尺与老鼠。通过眉间尺对老鼠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发现了眉间尺的“不冷不热”的性情。残雪在文章《艺术复仇》中说:“老鼠从里到外都令人憎恶,但它也同他一样是一条生命,在遇到大难时也同他一样会有着求生的本能,将心比心,眉间尺对它产生深深的同情是很自然的。可是这种同情心却是大忌,老鼠只要活着,就要继续对他作恶,于是他杀了老鼠…”②这是从同情心方面来谈眉间尺的软弱。
同时我认为,作者选择老鼠作为第一个恶的形象,是与后面的王这个恶的形象作对照,老鼠与王同为“恶”的形象,不同点在于老鼠相较眉间尺来说,是弱者。而王相较眉间尺来说,是强者。对强者进行挑战,似乎很庄严,而对落水的老鼠进行攻击,就不那么庄严了,反而催生出攻击者自身的同情心理。因为对弱者的同情是人的天性。以及,对弱者施行暴力带来的心理负担:
“……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只听得吱的一声,他蹲下去仔细看时,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大概是死掉了。
他又觉得很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他蹲着,呆看着,站不起来。”
小说不同于《野草》诸篇及其他篇什,采用“复仇”二字,而是多用了“报仇”二字。“复仇”从字面上来感受,更多透露出悲壮美。而鲁迅则刻意消解这种美感,用了世俗化的“报仇”二字。“复仇”用在眉间尺与王之间是合适的,却难以用在眉间尺与比他还弱小的老鼠之间。“复仇”固然壮美,但却容易姑息了对老鼠这样的作恶者的打击。这是作者对表面的“善行”(手段的“善”)与结果的“善”之间作出的选择。并且,由于鲁迅性格的现实性与功利性,选择了结果的“善”,这就必然带来手段的“非善”,而这种手段的非善带来的心理负担的问题,通过小说后面的部分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铸剑”。
鲁迅认为,不能因为恶人是弱者,就不予打击。因为其为恶的性质,是与强者相一致的。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著名立论。同样有趣的是,老鼠同样是“扑通一声”落在了水瓮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初发表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而《铸剑》(《眉间尺》)发表于192 7年4月、5月的《莽原》2卷8、9期上。可以说,这个《铸剑》细节是在延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立论,提出“恶”者不论强弱,都应打。
这是在给人们指路。是在总结血的教训,为后来者提供血的经验。而在作者的精神层面,则是一种排除多余自然情感的思考。
“你么;你肯给我报仇么,义士?”
“阿,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
“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债鬼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所以,宴之敖自己主动从心里清除了相关联的自然情感,最终,只剩下了纯粹的复仇。
正如《这样的战士》一文中描写的战士,“但他举起了投枪”五次出现,表现出战士对“战斗”的彻底性,“韧”性。仿佛我们看到了不为一切外物与感情所动的投枪机器,这便是“自觉排除”了“柔情善意”后,取得的效果。
那么,排除自然情感是如何与《铸剑》相结合的呢?或者说,铸剑的意象是怎样暗示和象征了排除自然情感的行为的呢?
“当最末次开炉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哗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第一,剑是金属,象征了一种与软弱相反的强硬气质。
第二,剑最后变成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冰是与热的、暖的感情相反的,散发出冷森森的寒气。
第三,剑本身的属性是为了伤人的,攻击的。
那么,铸剑的过程就是从软弱向强硬,从温暖到冷冰,从不伤人到伤人的过程,这个过程,象征了剔除了人作为生物的原始情感,剔除掉“除恶”带来的心理负担(手段的非善)从而排除自然情感以利复仇的行为。
三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复仇的现实性目的也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个体性的目的,即眉间尺为父亲复仇的目的。其二是社会性的目的,即改造社会。
通过排除自身多余的自然情感,从而达到了复仇的现实性目的(个体性的)。但是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复仇的牺牲,并没有带来更多现实性目的(社会性的),即未能改造社会。小说结尾处,麻木的看客再次出现,暗示了复仇的社会性现实目的的失败。
在眉间尺复仇受挫之后,他遇到了这样的情境:
路旁的一切人们也都爬起来。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了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得浑身发火,看的人却仍不见减,还是津津有味随的。
鲁迅通过这样的描写,表达出复仇的社会性目的难以达成,看客与闲人万年长存。同时,与壮美的复仇之旅不协调的是,眉间尺不得不纠缠于这种零碎繁复的纠纷里,脱身不得。表面上看,终极目标是杀掉王,这种纠缠只是一种无奈,其实,改善国民性、改造社会,才是复仇的终极意义。现在终极意义非常渺茫,个人的恩恩怨怨又何必了结呢?
如果说复仇的终极意义——改造社会,难以达成的话,那么个体的复仇还有什么意义?鲁迅似乎感觉到了复仇的虚无。这是鲁迅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促使了作者为复仇寻找另外的意义。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样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的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为什么帮眉间尺报仇呢?“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可以说,报仇的现实性目的,已经不是(不全是)他帮眉间尺报仇的目的。那么,这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报仇”本身,也即铸剑本身)
小说最初于1927年4月、5月发表于《莽原》2卷 8、9期时,题为《眉间尺》;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又改题为《铸剑》。
我认为,作者有意将一个动作性的词“铸剑”来替代名词性的“眉间尺”,正是为了突出铸剑的进行、铸剑的过程。是非剑到剑的中间状态。这篇小说就是要揭示作者理解与实践的这一生命过程。
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值得注意:宴之敖向眉间尺要两件东西,一是剑,二是头。而身体则作为多余的“负担”,被清除出去。
一般来说,头是隐含着指挥的、思想的、精神的取向。
而身体则隐含着盲目的、本能的、肉体的取向。
所以铸剑的过程也是灵魂摆脱肉体制约,以获得自由的过程。这个获得自由的过程要通过复仇或称铸剑来实现,那么,获得自由的过程就成了复仇与铸剑的新意义。也就是说,现实性目的的达成,成了获得精神性目的的手段。
眉间尺、王、宴之敖三个人物的次第出现,表现出了作者对复仇哲学得以成立的三要素的抽取。
首先,眉间尺代表的是凡人。由于鲁迅接受过尼采的思想,“不冷不热”的眉间尺(早期)更多地具备“庸众”的特点。他是一个尚未觉醒的人,一个未能摆脱肉体局限的普通人。
而后,在母亲的叙述中,王出现了。王作为复仇的对象,是主人公(庸众)觉醒的必不可少的因素。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爱我的敌人。”就是发见了敌人对意义生成的重要性,敌人是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剑”如果没有砧砍的对象,本身就失去了“剑”的功能,失去“功能”的剑不能称之为剑,而只是物质意义上“剑”形的钢。另外,敌人能够激发庸众的复仇心理。小说中有一细节:
“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眉间尺赶紧问。
“没有回来!”她冷静地说。“我四处打听,也杳无消息。后来听得人说,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就是他自己——你的父亲。还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
查《铸剑》出典,未有此细节之记载,所以可以定论,这个细节是作者添加的,是有意为之的。
制造眉间尺的父亲“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的王,激发了眉间尺的复仇意志:
“眉间尺忽然全身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
最后,宴之敖出现了,他代表的似乎是“复仇意志”本身,而复仇意志只有在复仇过程中呈现,“复仇”的完成,似乎也即是“铸剑”的完毕。但是,“复仇”的完成,“剑”的意义也消解了。这三个人物表现出了作者认为的复仇三要素,这三个要素是相互交融,缺一不可的。
小说结尾处,眉间尺的头、王的头、宴之敖的头无法分辨。就暗示了三者互为因素,又相互交融的结果。而在同一个金鼎内的蒸煮,又暗示了三者互为因素、相互交融的过程。最后,三者合为一体,不可分辨(三头共一身),却又各自分明(三个因素),暗示了鲁迅的生命哲学是一个过程的哲学。可以用“铸剑”、“复仇”、“走”之类的字眼来概括。
四
如果说,砍下王的头,是对王砍下父亲的头的复仇的话。那么,分别砍下自己的头的眉间尺与宴之敖,就是在进行对自己的“复仇”(反抗、反思、批判)。这种对自身行为的反省,是鲁迅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色,这样才能不断进行现实层与精神层的自我超越。亦即复仇的精神性目的。
鲁迅曾说:“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逐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③
1,对眉间尺的复仇(反省):对不能成事,优柔寡断的肉体(庸众)的复仇(反省)。受肉体局限的主人公便是未觉醒时的作者自己,鲁迅首先完成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复仇。主人公自己砍下了自己的头,并将头献给代表“复仇意志”的宴之敖,就是一个自己反思反省自己,并获新生的过程。
2,对王的复仇:这次的复仇是现实层面的复仇,亦即现实目的的完成(即上文所说的个体性目的),便是进行对敌的砧砍,并从这砧砍中,形成“剑”的意义,砍敌人的过程(包括准备),同时也便是“铸剑”的过程。
3,对宴之敖的复仇(反省):对“复仇意志”的反省。“复仇意志”要求人脱离肉身的限制,摆脱因选择“结果的善”而行使“手段的非善”的心理负担。但是,人的精神是与肉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周国平曾分析:
“我们一生中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来伺候肉体:喂它,洗它,替它穿衣,给它铺床。博尔赫斯屈辱地写道:‘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还有更屈辱的事:肉体会背叛灵魂。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扬,一个灵魂高贵的男人可能终身残疾。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跛子。而对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调整,肉体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着不屈的灵魂同归于尽。
那么,不要肉体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们将不再能看风景,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读书,散步,运动,宴饮,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爱情这件无比美妙的事儿。原来,灵魂的种种愉悦根本就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幽灵,不复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比死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修改帕斯卡尔的话:肉体是奇妙的,灵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④
所以,“复仇意志”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就像彼岸不可能真正到达,“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2]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⑤所以说,“剑”永远不可能“铸成”,精神性的目的的完成是虚妄的。
4,对“复仇完成”的复仇(反思、反省):小说最后,看客再次出现,显示出“复仇”的最终结果未能改变社会,现实性的目的(即上文说过的社会性目的)的完成是虚妄的。
五
如果说,只有剑变强了,才能战胜强敌,而敌人越强,想要战胜敌人就需要更强的剑。所以,剑变强(铸剑)是胜敌的手段——现实层面。又由于现实层面的胜不能改变社会,即不能真的胜,故此,胜敌的目的的意义被消解。
同样的,只有剑胜了敌,才能证明剑的强,而敌人越强,剑胜敌所显示出的剑的能力越大,所以胜是证明剑变强(铸剑)的手段——精神层面。
在鲁迅这里,复仇的现实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所以,“铸剑”(复仇)就成了他的生命哲学。所以,对王的复仇就成了行使生命意义的手段。至此,手段与目的相互交融,只有变强(铸剑),才能杀掉王,杀王是最初的目的,到后来,目的又转变为行使生命意义的手段,杀王之后的现实结果反而与意义无关。所以,当王真正被杀的一瞬间,主人公的头与黑衣人的头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
钱理群教授写道:“可以说,就在这‘四目相视,微微一笑’中,黑的人和眉间尺的人格和精神都得到了完成,或者说,鲁迅用他那诡奇而绚丽的笔触,将复仇精神充分地诗化了。”
也可以说,鲁迅终于寻得了自己的生命哲学。他当然看清了希望的虚妄,看清了所有努力很难得到收获(社会性现实目的),但他又不因绝望而放弃前行。他自己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这种哲学有些向死而生的意味,其现实目的依然是存在的。现实目的与精神目的相并存,相支撑,是鲁迅生命哲学的一大特色。
鲁迅至死躬行了他的哲学,他在1936年9月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六
鲁迅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这个自我意识不等同于自私或个人主义,而是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不能容忍自我存在的虚化,即自由意志。鲁迅的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这种哲学与鲁迅的生命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此称之为生命哲学。研究这种创造性的生命哲学,我们应该首先分析创造的性质。
创造有很多种,例如音乐创作、写作。区别于现实世界,人的创造可以是一种纯精神性的创造,而脱开(相对)现实世界对其的作用与干预,从而使创造的“可能性”近乎无限。这种可能性是创造的分母,而个体的创造本身,就是在这个分母范围之内的分子。而分子的大小取舍,则完全归结于人个体的选择。每一个创造都是独一无二的。一篇文章便是无数选择的结果,其选择的对象是所有的文字。而一段音乐也是无数选择的结果,其选择对象是所有的音符。文字与音符的全体是这种选择的分母,而选择的结果就是在分母范围里选择出来的分子。而选择的权利来自个体的每一个人自己,在这种选择中,人确定了“自我”的存在。相较这种纯精神的创造,鲁迅的哲学创造与现实相结合,所以,鲁迅不是纯粹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知识分子兼艺术家。
创造具有超越性,每一件创造物都是创造者此时此刻创造水平的体现与证明。所以,创造的作品本身具有等级优劣。而每一件创造物都证明着创造者的“可能性”,都是其“可能极限”。所以说创造者对创造能力与水平的提升,是证明了自身对“可能极限”的突破。
鲁迅的哲学是与生命,与社会相联系的。其社会性则凸显出这种哲学的道德性质。那么,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的道德。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一种对人作为动物,在动物本能基础上产生的行为的“违逆”。人是一种动物,而动物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道德就是改变这种原始行为法则的新形态行为法则。而这种行为法则并不以“强制”的形式来推行。(当然,是有程度的区分的,超出一定程度,则有法律来框范)而是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人非神,神完美无缺,绝对道德。人是动物又区别于动物,动物依靠本能,不存在“道德”的概念。
而道德也是一种程度的体现,从动物到神(应该注意,这个神并不确指神,而是指人心中构想出的“完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道德的有无与高低。人的道德选择决定了人在动物——神之间的坐标刻度。每一次道德选择都是一种程度的展示,都是其“可能极限”的证明。都是对“局限”(本能)的超越(克制),都是人脱离动物向神迈进的明证。
由上述分析得知,人的道德与人的创造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同特性,即:选择性(主动性)与超越性。
而这两种特性都取决于人的“自我意识”,即“自由”感的觉醒。
鲁迅的生命哲学,兼具了道德与创造,即是社会化的,又是纯粹精神化的。并且通过手段与目的相互交融(现实目的是达到精神目的的手段,精神目的也是达到现实目的的手段),使鲁迅的生命本身成为了一种创造,成为了一种“自由”的形式。也使得鲁迅的“自我意识”得到了最大化体现。
冀翼,80后写作者,思考者,公众号:妄想症患者病历本。欢迎订阅。
①《鲁迅与周作人》 13页
②《残雪文学观》 154页
③转引自《鲁迅作品十五讲》 121页
④《周国平文集》 第二卷 177页
⑤《病隙碎笔》 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