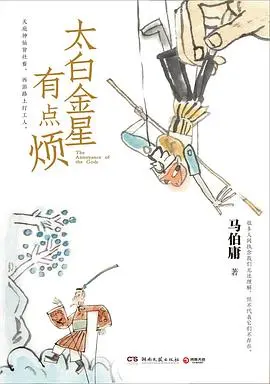电子书下载地址
内容简介
《地下室手记》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由主角地下室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地下室人是名年约四十岁左右的退休公务员,他的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全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内容探讨了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议题。第二部分是地下室人追溯自己的一段往事,以及他与一名妓女丽莎相识的经过。
《地下室手记》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也预视了他后来5本重要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该书也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认为:”这部小说是他写作生涯的顶峰,是他的扛鼎之作,或者,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是打开他思想的钥匙。”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俄国作家,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
他洞悉人类灵魂的奥秘,对人类心理活动有深刻的描绘
作品翻译超过170 种语言
其文学风格对 20 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发了卡夫卡、加缪、福克纳等作家
代表作有《穷人》《白夜》《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曾思艺
1962年生于湖南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翻译家,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译作有《俄罗斯抒情诗选》《尼基塔的童年》
《自然·爱情·人生·艺术–费特抒情诗选》等
读书笔记
文/宝木笑
传说仓颉造字时,天地变色,鬼哭神嚎,只因文字传世,天机因而泄露。文学作为文字聚变后的菁华,越是极致的作品,往往越会产生深邃甚至神秘的作用,不仅是对于读者而言,更是针对文本创作者本身。毕竟文学是由人创作,是人在其中以自身精神为药引,因而一旦一个人的思想进入到一种极致的状态,他的作品和他自身也将实现某种融合,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文论中提到的“化境”的概念。只是这种融合往往意味着一种沉重的代价,或者承载着某种苦难,毕竟生活之路充满荆棘,一种能够震撼到整个人类精神层面的思想,从来都不是轻易可以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个让文学史为之驻足的名字,有人曾说他的书比托尔斯泰伟大,比司汤达深刻,比阿加莎•克里斯蒂惊心动魄,如果真的要谈到世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誉,实在有太多可言。鉴于因为种种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内并未得到与其相称的评价,这里不妨简单引述一些这样的赞誉,权作一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名:
爱因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的影响比高斯都多。”
弗洛伊德:“陀是唯一值得看的作家。”
卡夫卡:“陀翁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茨威格:“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齐克果是人类的精神领袖。”
博尔赫斯:“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
至于加缪整个反抗体系对陀氏的继承,纪德对陀氏的五体投地等事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即深刻的影响性和评价复杂的不对称性,他和他的作品仿佛地火在黑暗处运行,人们能够感受到他的燃烧却看不到那火焰的光芒。这与陀氏个人的性格、经历特别是其作品的手法和主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其流放西伯利亚之后的作品,《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每一部都带着鲜明的陀氏风格,暗色的基调、心理的二重剖析甚至对变态行为的刻画……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其中救赎的旋律和陀氏独有的反省和思索,这也难怪,毕竟在黑暗处,人们只能感受到热,继而会抱怨没有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为什么要选择《地下室手记》来讲述这样一位“说不尽”的伟大作家,难道上面那五部巨著不能代表陀氏的一切么?显然不是的,但就像心理分析往往要追忆对象的童年回忆,甚至不惜进行催眠一样,如果我们分析陀氏整个一生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地下室手记》其实是一个分水岭。虽然之前的《穷人》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已然显示了陀氏的才华和某些风格,但从《地下室手记》开始,陀氏的小说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轨道,《地下室手记》预示了他后来5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基调,而这5部长篇构建了陀氏的文学思想内核,因此完全可以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引燃陀氏地火的星星之火。
显然,这星星之火迸发得过于诡异,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谈到《地下室手记》仍然争论不已,想那“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已经足以成为文学史上最为妖异的开篇。而后面的故事比起这开篇丝毫不遑多让,用现在流行的话也许就是“全程无尿点”,将压抑进行到底也一直是陀氏中后期作品的毒蜂之刺。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地下》时间是“现在”,1860年代,“地下人”是名年约四十岁的退休公务员,他的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在他的自言自语中,围绕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议题,直接应战“先生们”的理性体系,就像一篇形式自由的论文。第二部分《雨雪霏霏(或译关于湿漉漉的雪)》,“地下人”开始叙述大约十五年前,即1840年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以及丽莎之爱,这一部分里,“地下人”进一步吐露自己的苦闷,继续评判“先生们”的理论。
《地下室手记》手稿
这原本很可能是一个“枯燥”的故事,仿佛无尽黑暗处的无尽沉闷,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点燃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地火,让“地下人”成为永恒的经典形象载入文学史册。因为“地下人”和之后许多带有陀氏标签的形象虽然并非文学史上的首创,但在陀氏手中变得更加彻底和癫狂。“地下人”绝非正面形象,准确地说是一个边缘化至近乎病态甚至变态的人物,他如仓鼠般生活在地下,在黑暗和潮湿中逡巡徘徊,自言自语,他与人接触时敏感而脱节,甚至用情感折磨的方式快意于妓女丽莎的痛苦。总之,这个由果戈理的小人物演变而来的形象,这个如地下丧尸一般的彼得堡人,同样带着那个时代浓浓的彼得堡式的自我矛盾。
然而,这种“反英雄”式的小人物设定只能让“地下人”成为典型,却不足以成为经典。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当然也不会将人物塑造仅仅止步于此。“地下人”是带有一种与其身份和状态截然矛盾的“圣灵感”的,用书中的意思就是地下人的主要特点是“过度的意识感”,而这“过度的意识感”仿佛一把双刃剑:“地下人”比别人思想更加深邃,能够多想一步或几步,见常人不见,且善修辞,通逻辑,旁征博引 (按照西方文论的说法是,他的语言有互为文本性);然而另一方面,“地下人”想得太多则无法行动,愈加自卑自虐,自相矛盾,是一种病态,这一点“地下人”自己毫不掩饰:“我向你们发誓,先生们,过度的意识感是个病,实实在在是个病”,这让他不会与他人相处,心里渴望爱,但是不会爱,自虐和虐他倾向的并存阻碍了他爱的能力。
如果一定要概括陀氏人物的形象特征,那么“地下人”无疑可以成为某种标准,他们的缺点和病态仿佛让人恐惧的冰冷和黑暗,然而他们的内心又仿佛运行的地火,让人能够感受到温度和燃烧。《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福把当铺的老婆婆杀死,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病态的事情?其一为贫穷,其二为他所构思出的一套“杀人理论”:“在世上,某些强人,被选择的人可以踏着别人尸首而前进,”于是其通过杀人去证明自己是强人,但他内心不安,痛苦挣扎,直至遇到娼妓索尼娅,两人相濡以沫,最后拉斯科尔尼福被流放,索尼娅一直相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家境富裕,但父亲是吝惜鬼,父亲和大哥在争夺同一个女子,伊凡怀疑上帝,怀疑一切(《宗教大法官》一章实在精彩,那种对宗教的终极拷问,个人觉得无人能出其右),有一套从推翻上帝意义得来的杀人理论,他有意无意把这告诉父亲的私生子,私生子把父亲杀死,伊凡不堪重负,最后发疯……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小说史上从来不缺少描写人物压抑和病态的篇章,但为何唯独陀氏在其中成为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巅峰,成为后世无数以解剖人性著称的大师们共同的“精神导师”?这一切将在《地下室手记》中找到答案,前面提到的“矛盾感”在其极具个性的创作手法中得到了完全的迸发,二元论的人物塑造从来不是陀氏的发明,但陀氏却将内向挖掘人物自心发挥到了极致。而这种发掘绝非一些文学研究者所说的属于“心理学延展”那样简单,而是通过人物在一种极端条件下的自我思想和魂灵自述来实现的。我们会发现陀氏小说的主要人物都处在一种边缘,就像“地下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发疯的边缘,他不断地提出想法,不断地否定自己,他肆无忌惮地宣泄思想,他颤抖于心灵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将人物推向绝境,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一切完全暴露,这就是陀氏的人物塑造,这样的手法并不神秘,却让无数作家望而却步。
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谁也不能逃脱世俗的眼光,阮玲玉遗言说“人言可畏”并非偏激,而是所有人身上无形的枷锁。本来能够体察人类灵魂深处那种细微的地火就已经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神迹”,而当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认识到一旦自己按照心中的指向将之付诸笔端,也许会带来弥天谩骂甚至大祸,按照人类趋利避害和虚荣的本性,他们是会选择回避的。但仍有人选择了继续向前,在描述人物内心那种使人深深恐惧的黑暗方面,我所见只有福克纳和穆齐尔略可与陀氏比肩。无怪乎尼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他大声地宣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一位能使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我把和他的结识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
令人惋惜的是,就像尼采一样,在陀氏的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条伤感的原则:敢于直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地火并令其燃烧的人,终将付出惨重的代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为复杂、最为矛盾的作家,这位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一起被称为俄国文学三巨头的伟大作家一生坎坷。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患有癫痫症,一生都未逃脱病魔,16岁母亲死于肺结核,18岁父亲死于非命(至今说法不一),24岁凭借《穷人》一举成名,却在28岁因为涉及反沙皇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的一刻才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在那荒凉贫瘠的西伯利亚,他的癫痫症发作愈发频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巨变。
陀氏小说的创作和这些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这样的极端情况最能催生人的思想质变,难以想象如果曹雪芹家族没有蒙难,也许清中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再多了一部《金瓶梅》而已。当然,没人愿意经历这样的极端,这本身就带着自觉或不自觉成为人类思想殉道者的味道,而这是所有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但事情并未结束,1864年终于来了,在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兄长相继去世,他还需要照顾兄长的家人,这使得他濒临破产,他希望通过赌博来还清债务,却欠下更多债,整个人陷入消沉之中。但为了生存,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继续写作,其内心的焦灼痛苦和愤懑癫狂可想而知,无怪乎诞生于这一年的《地下室手记》,被许多人称为是其所有作品中最恶毒的一部。
我们能深深感受到那种绝望中的放弃,这种放弃是一种对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放弃,却是对自己思想的完全放任:
“无所谓了,反正生命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我知道迎合大众的口味能够改善我的生活,但我再也不想为活下去而卑躬屈膝了,即使我写的东西最终无人问津,或者被人唾骂,甚至我因此饿死,这都无所谓,我只要痛痛快快地写一次,将内心的东西完全写出来!”
笔者猜想,这也许就是陀氏当时的内心写照吧,所以我们见到了尼采一般的肆无忌惮,那人人躲之唯恐不及的地火,在陀氏的笔下燃烧,他义无反顾冲向黑暗,他不要任何收获,他只想随心燃烧,燃烧。
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转型,《地下室手记》成为后续《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总序,陀氏终于完全摆脱世俗的束缚,迎来了思想的绽放。当然这意味着更多的对抗和牺牲,我们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渐渐了解这位伟大作家,并仍然不能完全给予其应有的荣誉,实在是因为陀氏的思想从《地下室手记》开始就注定无法在很多土地上盛行。上学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3年写出的《怎么办》如雷贯耳,是的,1864年的《地下室手记》是针对《怎么办》的。如果稍微留意,我们会发现《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不是直接对我们说话,而是讲给特定的听众,他称之为“你们”、“先生们”,“地下人”一再模拟他们的观点和话语,实际上这完全是有所指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很多思想者主张“新人”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先生们”的人格象征,《怎么办》是那个年代思潮的“圣经”。其实,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著书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了坦诚交锋,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车氏的现代乌托邦,一是欧洲启蒙形成的现代思想体系,这两者都依赖理性传统,但对人性的理解却显贫乏,追问“什么是人性”开始成为陀氏小说的关注的核心。客观地讲,《怎么办》在美学上是失败的,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都缺乏真实的人性基础,而车氏笔下的未来是这样的:俄罗斯将会把大片的草原变成可耕地,将会用玻璃和钢筋造成水晶宫,在这个新世界里,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充分就业,男女平等,艺术繁荣,最重要的是,这个完美的世界由乐观向上、富有理性的男女组成,他们没有私利,因为他们可以在普遍的善中找到自己的利益和福祉。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怎么办》与《地下室手记》的这种对抗。陀思妥耶夫斯基遍尝人间苦涩,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苦役监狱里度过的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厚重的围墙,白骨般惨淡的阳光,晦暗潮湿、布满跳蚤、虱子和蟑螂的囚室,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受刑时的皮开肉绽,不堪忍受的体力惩罚,人性在极端条件下的扭曲……那四年的生活梦魇,彻底击碎了陀氏的空想主义理念,更严重的是,从西伯利亚归来,陀氏又遭遇了经济、感情、事业、精神的多重打击。正在这个当口,一部叫做《怎么办》的小说却开始风靡彼得堡,我们可以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心情,他可以接受命运对他的肆虐和不公,但他无法再容忍某些“革命者”对现实的扭曲。于是,他拿起笔,开始用文字点燃那黑暗中的地火。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陀氏的小说确实晦暗,这却在另一个方面成就了陀氏的传奇。如果我们整体翻阅陀氏小说,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不描写外界生活场景,即使出现这样的场景,陀氏笔下带过的白描也多是忧郁的,那些在街上徘徊的市民,他们的眼神是“阴沉着的”、“忧心忡忡的”甚至“恶狠狠的”。而这些词,严格地说都不是一种对外貌的描写,而是对某种精神状态的捕捉,我们在读陀氏小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悬空感,总觉得这些人处在要发生些什么的临界状态。谋杀、自杀、发疯这些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使陀氏小说的情节,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这都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遭遇社会现实的挤压后,非理性对理性的癫狂冲击。实事求是地说,陀氏的这种思维角度和作品意味,无论是屠格涅夫还是托尔斯泰都不具备,果戈理虽然也写出了市民社会的情景,但主要还是侧重历史进程中人性被淹埋的悲剧,唯有陀氏始终立足在个体的精神意识和内心解剖。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既然如此,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何用?
当我们每天像沙丁鱼一般挤在地铁公交中,眼前是无数同样苍白皱眉的面孔;
当我们困在格子间,不得不面对面前仿佛整日嘲笑我们的电脑屏幕;
当我们连在网络里也不得不遵循规则,忍受居高临下或是人性的灰暗;
当我们在深夜加班结束,走在霓虹闪烁却陌生冷清的街口,接到的却是上司大发脾气的电话;
当我们善良谦卑地向人群接近,收获的却是勾心斗角和轻蔑冷淡;
当我们用尽全身力气,却仍然无法改变自己卑微的身份,无法让亲人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青春散场,我们却发现自己也许永远拿不到下一站幸福的门票,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也许真的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们确实需要鸡汤和“光明的尾巴”。
但是,我们虽然可以佯装快乐,我们虽然可以强打精神,可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在回响——这强颜欢笑的一切真的是我们的人生么?有光明就有黑暗,生命意义不在于逃避的技巧,而在于冷静的直视,正是因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我们无论身处何样的黑暗,才会明白那黑暗处必有地火,虽无光亮,却在燃烧。而这正是陀氏思想和小说最大的精髓——我们不要粉饰的乌托邦,我们要荆棘丛中绽放的小花:
《罪与罚》中的妓女索尼娅为了维持穷困的一家出卖肉体,却又心灵纯洁,引导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向救赎之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在种种的恶行中最终回应善的召唤,完成了自我救赎;就连一直在矛盾中癫狂的“地下人”,其实在内心最深处仍然期待的是人性的觉醒,他认真地告诉“先生们”:“如果你们仔细看看我的故事,会发现我身上比你们身上有更大的生命力……现代体系下生活的人,宁做抽象的人,而害怕做有血有肉的个人。”如此,也许黑塞才是最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而他的话就像在为我们回答上面的所有问题:
“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当我们孤独苦闷,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时,当我们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疯狂而美丽的残酷,并对生活一无所求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去聆听这位惊世骇俗、才华横溢的诗人的音乐。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欣赏者和评判者,而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爱难者共命运的兄弟,我们承受他们的苦难,并与他们一道着魔般地投身于生活的旋涡,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盘。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墓,陀思妥耶夫斯基临终说的最后的话是给妻子的,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怜的……亲爱的……我能给你留下什么呢?……可怜的,你今后的日子该多么难啊!”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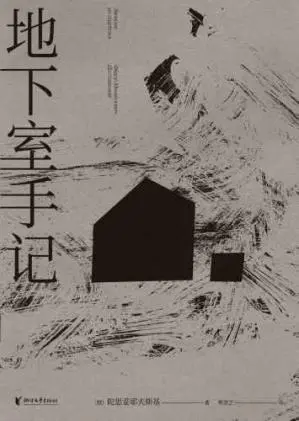



.1bctlxu0g7k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