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下载地址
内容简介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本书是关于柏拉图中期理念论和美学思想的一篇重要对话。对话所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对话主要由七篇对爱神的颂辞组成,这七篇颂辞层层深入,讨论的主题从对爱神的赞美转向对爱的本质的追问,又提升到爱神帮助之下灵魂对知识的求索,最终引至美的理念引导之下灵魂向纯粹理念世界的不断攀升。
作者简介
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本书是关于柏拉图中期理念论和美学思想的一篇重要对话。对话所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对话主要由七篇对爱神的颂辞组成,这七篇颂辞层层深入,讨论的主题从对爱神的赞美转向对爱的本质的追问,又提升到爱神帮助之下灵魂对知识的求索,最终引至美的理念引导之下灵魂向纯粹理念世界的不断攀升。
读书笔记
前苏格拉底的哲人赫拉克里特仅存的《残篇》中,每一句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都蕴含着石破天惊的巨大力量,比如这句话: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本是同一条路。因此,在诸多对《会饮》的解读中,当人们熙熙攘攘都去讨论爱欲的上升时,一个叫做Sean Steel的学者就抓住了老赫这句话,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会饮中的下降》这篇颇有才华的注解文章。
抓住苏格拉底的下降并非Steel的独创,因为全部柏拉图的对话都可以看作苏格拉底的下降,在那个洞穴的比喻中,就是苏格拉底看到光之后不忍丢下那些依旧身处黑暗中的人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从而再次只身返回洞穴,试图用自己出洞的经验去引导其他人也一同走出那幻像的世界。这种返回似乎已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人,是已经完成了上升之后的下降。上升和下降,似乎并没有同步。但是在这篇众人都为那奇迹般的爱欲攀登激动不已的时候,Steel的贡献在于他让我们看到,即使这般看似纯粹地上升,也是和下降同步进行的,合而为一的。
我们看到,从不讲究衣着的苏格拉底非常罕见地沐浴更衣,甚至还穿了鞋,去赴一场华丽的名流晚宴,艺术party了。盛装,如同修辞,都是伪装与矫饰,看来这次,苏格拉底是决心一头扎到俗世中,收敛锋芒,和光同尘了。穿了鞋,也便隔绝了大地。今天的苏格拉底,从未有过的谦卑与随和。那是阿伽通获悲剧最高奖杯的华彩之夜,是奥斯卡或者格莱美之夜。然而就像后来卢梭所痛斥的那样,艺术达到颠覆的时刻,便是文明被败坏之时,过分的纤弱和精致,打破了文与质的平衡,文胜质则史,一个文明少了manliness的强悍,便显得孱弱与琐碎。就像后人评说诗情蓬勃的雅典败给了粗野骠悍的斯巴达,文化最繁华的汉宋也葬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元手里一样。那么,阿伽通的胜利之夜,是否也标识着雅典城邦的败坏之时?
果然繁华,果然奢靡,果然绚烂。全雅典最美的、最有才的、最著名的人都在这里了,美酒、美言、美人,金光灿灿。苏格拉底终于听不下去了,质问难道对爱欲的赞誉可以如此虚假和奉谀么,可以不知道羞耻么?在这一刻,他决心另起炉灶,以一人之力,扭转乾坤了。也是在这一刻,他站在雅典的美和艺术最辉煌的顶端,以及雅典城邦之德性最败坏的深渊,开始了他的行程,用句最热门的话,开始了他“一个人的奥林匹克”。Steel把参与阿伽通晚宴的人们都称作“魂游”之人,一群灵魂迷失了理性的主宰,被埋葬在身体爱欲中的人。当灵魂失却了统帅的力量,沉沦于身体欲望的时刻,便如同游魂一般,不复为人了,而形同鬼魅,飘荡在世间。苏格拉底以一人之躯独赴游魂的盛宴,胆识也的确不同常人了。然而更加诡异之处在于,这群失却了灵魂爱欲的人,埋葬他们爱欲的恰恰是泛滥的身体爱欲,一群爱欲太盛的人反倒是缺乏爱欲的人,岂不怪哉?那么试图重新激发起他们的爱欲去拯救他们的苏格拉底,岂不是在玩着一场最危险的游戏:身体的爱欲能否顺利转化为灵魂的爱欲?或者说,孰知被激发出来的新的爱欲,不会重新叠加在身体爱欲之上?以火灭火这种奇招,也只有苏格拉底想得出来。
Steel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意象,把它比作奥德修斯的冥府之行。奥德修斯为了返乡,来到冥王哈得斯的地府,召唤出死去的幽灵,用牺牲之血,让它们获得短暂的生机,以获得返乡之路的指示。Steel称,苏格拉底用以召唤这些幽灵的牲血,就是他的言辞,他的辩证法。然而在奥德修斯的故事里,牲血无法真正地让游魂还阳,短暂的获得生机,其功能只是打通阴阳之隔,打通阴阳对话的能力而已。女巫第俄提玛的险峻之辞,并未真的惊醒众人,赢来“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倒吸一口凉气的清醒,反倒获得声声喝彩。这喝彩,和阿伽通漂亮却不知耻的虚假言辞赢得的喝彩并无二致。这喝彩,湮灭了阿里斯托芬可能的唯一真实的驳难,也湮灭了苏格拉底试图唤醒游魂的努力。而且,他败得毫无痕迹。阿尔喀比亚德的怨妇控诉也进一步证实了苏格拉底言辞的失效。苏格拉底试图用貌似身体爱欲的接近与引诱导向真正的灵魂爱欲,在阿尔喀比亚德那里反成了耍弄和背叛:你勾引我,又甩了我,不是在耍我么?曾经订立的跟随苏格拉底一同上升的爱欲盟约,因为阿尔喀比亚德的不堪忍受和逃跑,成了一场爱欲的闹剧。上升失败后的结局,不是继续沉沦于身体的爱欲,而是被激起更大的爱欲的渴望,无法在升华中实现,只能在向下的败坏中变本加厉地膨胀。上升失败的结果不是回到起点,而是加速的沉沦。
整个阿尔喀比亚德的控诉中,最令人惊奇的特质就是苏格拉底的沉默。似乎他的沉默只是印证了阿尔喀比亚德言辞的真实。后世善良的学者们将诚实区分为“真相的诚实”与“伦理的诚实”,说阿尔喀比亚德的所谓“酒后真言”虽然说得不假,但在道德上却不诚实,以此针对阿尔喀比亚德对苏格拉底的控诉来进行辩护。然而他的沉默又焉知不是苏格拉底的某种放弃?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教育失败之所以成为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因为倘若连苏格拉底最看好、最有前途的弟子和未来的政治家都不堪忍受哲学的折磨和枯寂,结果中途逃跑的话,那么能够有如此强韧神经去忍受哲学的又有几人?这个失败是否对哲学的教育是个致命打击?在阿尔喀比亚德身上失败之后的苏格拉底,何以还能够如此乐观地试图教育宴会上这些资质要差得多的人?在放弃了对阿尔喀比亚德的教育之后,为何他依旧不放弃自己辩证法的引导之路?
奥德修斯牲血召灵的隐喻似乎也在暗示我们,苏格拉底似乎并非不知道召灵的短暂性,也就是说,他比谁都明白自己辩证法召灵的最终无效性,不会比阿尔喀比亚德的结局更好。既然如此,他盛装出席的召灵大宴又所为何来?如果他只为了独步登上第俄提玛的爱的高峰,那么这个过程他早已完成,又何必冒险下到冥府,来完成这并不可能的上升?他盛装出席的冥府之行似乎只是为了展示事先就知晓的失败,那么他这个失败又在展示给谁看?又是为了什么?一夜的欢饮之后,所有的人都醉倒了,睡去了,如同那冥府中的幽灵们,在牲血的刺激失效后,再次回到了飘忽游荡的状态。只剩了清醒的苏格拉底,掸掸身上的尘土,再次出发了,如同奥德修斯一样,他也要“回家”了。如果说下到冥府的奥德修斯已经获得了归家的指示,靠了幽灵们“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话,那么下到欢饮游魂中的苏格拉底又获得了什么?
临别前的最后一场谈话,是苏格拉底和悲剧诗人与喜剧诗人畅谈是否有一种诗可以超越悲剧与喜剧之上,可以兼具悲剧与喜剧?这似乎给了我们一点晦暗的线索,苏格拉底的冥府之行的全部,他的失败的辩证法的拯救,便是一部超越了悲剧和喜剧的哲学大戏。它如同阿里斯托芬的讽刺一般向后人展示了哲学家拯救城邦于危亡之中的不可能,最多不过是如牲血一般换得一群幽灵的苟延残喘。苏格拉底所赢得的游魂们死亡般的喝彩,以及阿尔喀比亚德的幽怨,就是对他最大的讽刺。这是它的喜剧色彩,甚至它因此嘲笑了阿里斯托芬的嘲笑:你根本没有嘲笑到点子上,还不如我替你来嘲笑。但是这里柏拉图又何尝不是把苏格拉底绑在了献祭的牺牲台上,他的沉默,最终如同每一个悲剧英雄的沉默,做了祭坛上的牺牲。只是这个悲剧中,没有了人与神的和解,似乎苏格拉底这一趟下降,只是为了证实和加速游魂们的死亡,以及自己苏式救亡法的不可能。那么,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命运献祭给了何人?
悲剧中让英雄死亡的是神意与命运,英雄死了,神与人于是貌似相安无事,实则貌合神离,获得了形式上的短暂“和谐”,虽然这平衡终究因为不稳定而被打破。对话中让苏格拉底献祭的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沉默了,哲学与城邦于是貌似相安无事,实则同归于尽。苏格拉底魔力的言辞,貌似带领人们登上了哲学的峰顶,从而让后世那些没有看懂柏拉图用意的无数的哲学粉丝们山呼万岁,真的就摩拳擦掌,试图跟随苏格拉底继续攀登着爱欲的阶梯。殊不知柏拉图想说的正是这条路的艰辛与危险,甚至是此路不通。君不见那些欲登峰而跟不上的人死的很惨的下场么?一如阿尔喀比亚德的哀怨与毁灭,亦或阿波罗多洛斯之流“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忧郁与绝望。苏格拉底之后的爱欲攀登,注定要绕路它行,注定要先行下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一次性的死亡了。后世的“柏拉图主义者”们,不过是对柏拉图误读后的短暂还魂。城邦的守护者们也长舒了口气,庆幸着苏格拉底的言辞没起到什么作用。貌似苏格拉底失败了,他说完后,城邦里不还是歌舞升平,该喝的喝,该睡的睡,只剩他单人匹马回家了事么?神奇的苏格拉底,终究没能拖曳几个人跟随着他离经叛道。然而苏格拉底此行的招魂,似乎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城邦糜烂倒无可救药的地步:奋力一救而不成功,不是比全然不救更加宣布了无药可救么?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明知失败却依然前行的冥府之行的价值,似乎只在于他与魂灵们一拍两散,共同归于毁灭的瞬间。柏拉图让他的苏格拉底引爆了晦暗的冥府,这似乎是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恐怖主义的鼻祖。这种方法后来在绝望的现代哲人那里屡屡得见,一个个哲人不惜潜入现代性的最深渊处引爆自己,以期与烂透的现代社会同归于尽。他们的希望,只寄予被炸平了的废墟之上所摊开和展现出来的新的秩序与希望。
苏格拉底死前念念不忘的是用《伊索寓言》的题材来写作诗,为的是把自己生命中的梦描述出来,他一直以为应当用哲学来展现自己的梦,死前才明白应该用诗歌。而柏拉图在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念念不忘的是要写出一部三联剧的诗歌来,也不是被后人所认为的哲学。如果说他们都用哲学炸毁了病入膏肓、腐败到极点的城邦,那么他们被控告的败坏城邦的罪名,又焉知不是以毒攻毒的最后一招?而后世那些重新扛起哲学大旗的人们,又焉知不是与柏拉图的初衷南辕北辙?在哲学的废墟上,重新生长与抚慰的是新的诗歌,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没来得及写出来的诗歌。
硝烟渐渐散去,我们的视野渐渐清晰起来:在雅典的废墟和哲人的尸体之下,野花从裂缝中艰难地钻出,依旧烂漫,被遮蔽的存在慢慢地显豁了。奥德修斯们可以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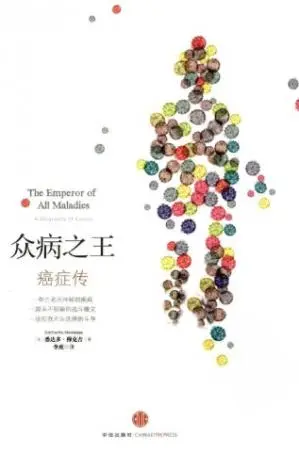
.5czcaj5tiy00.webp)